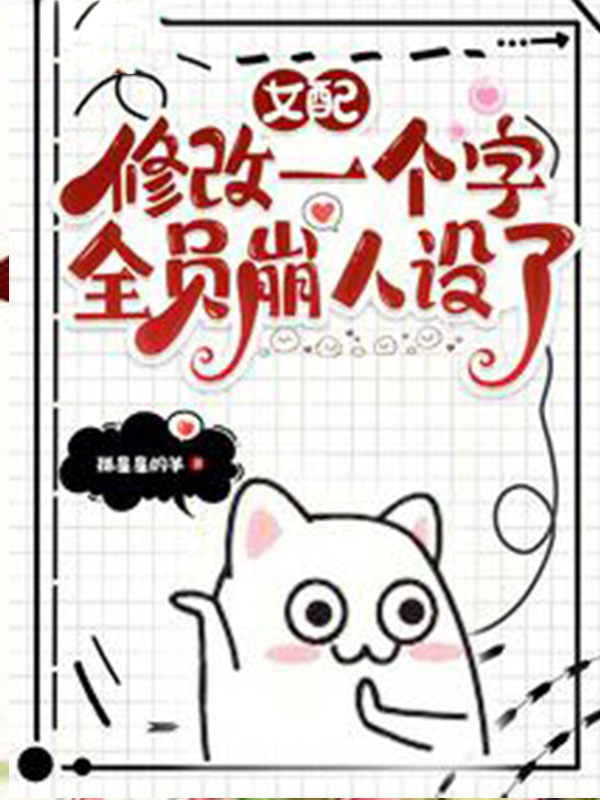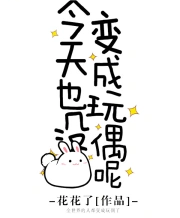晨曦初露時,悠悠醒來的人不經意對上一雙含笑的眼眸,身子下意識地想悄悄退開.
他長臂一勾,輕易將她再度納入懷中.
炙熱燙貼的觸感讓她渾沌的意識瞬間清醒,慌亂中低頭望去,入眼之處,兩具一絲不掛的軀體緊緊貼合在一起!
昨夜那真實得令人顫抖的夢境從腦際閃過,瘋狂的畫面讓她幾乎要昏死過去.
如他所料,暴風雨如期到來.
瘋狂的啃咬捶打後,她無力地看著自己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記,兩行清淚無聲落下.從頭到尾,他一聲不哼,安安靜靜地任由她發洩,粗壯的胳膊仍舊摟在她腰間,臉上滿足幸福的笑意未曾淡去半分.
見她哭得傷心,想低頭吻去她的熱淚,卻再一次勾起她的怨恨,恨極之時,她張嘴狠狠咬在他胸前,直到嘗到一股血腥的味道,才倏地放開他.
肌肉發達的胸膛上,她的齒印清晰可見,甚至正冒著絲絲殷紅的血.她癡癡盯著那傷口,一時間竟分不清到底是在恨他還是在恨自己.
擡頭看他,他仍是含笑看著自己,她鼻子一酸,狠狠罵了句"白癡",眼淚又淌了一臉.
他仍是低頭為她吻去淚水,這一次,她沒有再拒絕,隻默默承受著他的溫柔.那個仍冒著血的傷口實在刺眼得很,她吸了吸鼻子,想找個東西為他止血,視線裡卻一無所獲.大滴的血珠仍在冒出,她扁了扁小嘴,想到他曾為自己所受的傷,心底一酸,情不自禁地把嘴唇湊了過去,輕輕為他tian乾血痕.
不料,她這舉動惹得他渾身一緊,一聲低吼後,他驀地翻身,滾燙的雙唇瘋狂落下.她拚命捶打掙紮,驚慌閃躲退避,他卻步步緊逼,絲毫不給她逃脫的機會.
弱肉強食的情海對峙中,無力反抗的人在淪陷的一刻用力咬在他手臂上,直到意識漸漸變得模之時,才緩緩松開,迷失在他炙熱癡迷的愛意中.
激情退卻後,一個仍在笑,一個仍在哭,他笑得邪惡饜足,她哭得動人淒楚.
昏昏沉沉地又昏睡了過去,再次醒來時,枕邊人已沒了蹤影,伺候的婢女們恭恭敬敬地立在紗幔外,靜候一旁.
拖著渾身酸痛的身子,在婢女的伺候下梳洗完,又吃了一堆大補的藥膳後,她在婢女的攙扶引導下緩緩到了客廳.客廳裡,馮素弗一身儒雅雪衣,渾身上下閃耀著她從未見過的溫潤氣息.他的身邊,一名與她年齡相仿的俏麗女子大方地牽著他的胳膊,不知聽他說了些什麼,正發出一串銀鈴般的笑聲.
那笑聲,不知為何刺耳得很.
她眉心不經意地輕蹙,一絲連自己都察覺不到的鬱氣一閃即逝.
馮素弗見到她,星眸頓時一亮,長身立起大步向她走來,唇邊那抹笑暖如春日.
"怎麼不多歇會?"他右臂剛想擡起,才發現身旁的赫蓮娜娜仍牽著他,不得以,隻好伸出左臂欲環過她的柳腰.
她瞟了他一眼,眼裡滿滿的都是鄙夷.這家夥,還想左擁右抱,想的倒是挺美.信步一閃,在他微微的驚愣間躲過他的魔爪,大步走向一旁的錦椅,款款坐下.
他隻道她還在惱自己,隻得無奈地走到她跟前,俯首輕聲哄道:"我們的帳回頭再算好不好?來與我坐一塊."
br>
她卻眼簾低垂,裝作沒聽見.
還想說什麼,他身旁的赫蓮娜娜卻已搶先道:"喂!
素弗哥在跟你說話,你怎能如此無禮?"
楊曦擡眼,視線微微掃過兩人.他一言不發,似乎認同了身旁那女子的斥責,正在等她賠禮道歉.她揚了揚黛眉,唇邊溢出一絲嫵媚的笑意,站起來躬身行禮,"對不起,少主,奴家知錯了."
馮素弗一下子傻了眼,完全搞不拎清是怎麼一回事."魔女......"
"少主如果沒其他吩咐,奴家先行告退了."她學著清宮戲裡的宮廷規矩福了福身,頭也不回地步出大廳.
他癡癡看著她清冷的背影,一時間竟忘了要追上去,等那抹飄逸的影子消失在門外後,才驀然清醒,再也顧不得廳裡其餘人,長腿一邁便追了出去.
"素弗哥,你要去哪?"赫連娜娜仍死死牽著他的胳膊,生怕他把自己丟下.
"追我娘子."這掛在他身上的家夥實在煩人得很,他大掌輕輕一揮,輕易揮開她的糾纏,雪色衣裳一閃,身形已在數丈之外.
負氣出門的楊曦隻覺得心中鬱結難舒,屏退所有婢女後,獨自一人跨入陌生的園林中.她不知自己為何要生氣,可一想到馮素弗與那女子的親昵,整個心胸便莫名的氣悶糾結!
這人,昨夜與今晨才對她......事隔半日,怎能就擁別個在懷!
這可惡的男人!
身後,尋了她半晌的人,看到她縴細的身影後,一顆莫名緊張的心頓時卸了下來.每次看到她從自己身邊逃開,一顆心便莫名地驚慌恐懼,好怕她又像從前般,隻隔短短數日,便把他完全排擠到心門之外.
他好不容易才往她心裡剛剛踏入了一步,不想也不能在此時再次遭她嫌棄厭惡.
他輕輕靠近,小心翼翼從身後摟緊她,"魔女......"
她微微一顫,下意識的抗拒:"放開我!
"
"不放!
"他雙臂稍用力,緊緊把她困在懷中,"你已經是我的人了,這輩子,我死也不會再放手."
聞言,她身子漸漸變得僵硬,一顆心也迅速冰冷了起來.
他們的關系為什麼會變成這樣?他們是叔嫂,怎能苟合在一起?他與誰在一起,與誰親近,她有什麼資格在意?
在這個亂世,女子算什麼?一夜情算什麼?與他來說也不過是一場春花秋月,旖旎春夢,她憑什麼以為與他有了肌膚之親,他就必須為自己守身如玉?
這豪華奢靡的冰聖宮背後所代表的含義以及勢力,她縱然猜不出十分,卻也能估摸到三四分!
如此一個身份尊貴的男人,豈是她這樣一個女人可以駕馭?
她到底在氣什麼在意什麼?誰給她這個權利和資格?